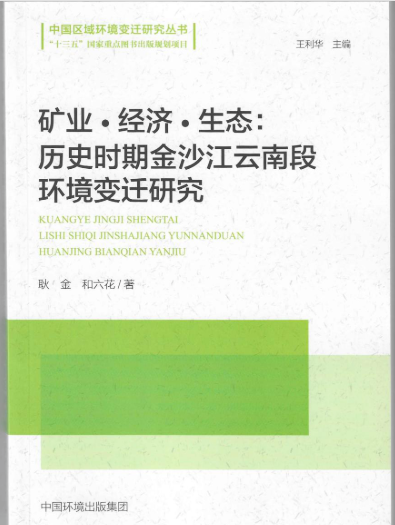
图书封面
书名:《矿业·经济·生态:历史时期金沙江云南段环境变迁研究》
著者:耿金、和六花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出版社:中国环境出版社
作者简介
耿金,(1987-),云南富源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西南环境史研究所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南史地、环境史、水利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校级社科项目2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项,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项,省级项目2项。目前已在《史学月刊》《思想战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中国农史》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
和六花,女,纳西族,1983年2月生于云南丽江,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为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副研究员、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主要致力于西南环境史、云南民族古籍及历史文化研究。目前已主持或参与国家及省部级科研课题多项,发表论文数十篇。代表作品有《云南少数民族非纸质典籍聚珍》《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集成》《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绘画》等。
目 录
绪 论
一、导言
二、学术史
三、章节内容
第一章 金沙江云南段自然环境与民族文化
第一节自然地理特征
第二节民族分布与社会概况
第二章 历史时期金沙江云南段矿业开采
第一节 金沙江云南段矿产种类与区域分布
第二节 历史时期金沙江滇西段的黄金开采
第三节 历史时期滇东北段的矿业开发
第三章 明清两季木氏土司势力扩张与资源掠夺——以金矿开采为中心
第一节 木氏土司势力在金沙江流域的兴起与经营
第二节 木氏土司在金沙江流域的资源拓展之路
第三节 木氏土司在金沙江流域的金矿开采
第四章 滇东北段的矿业开发与区域人口及农业发展
第一节 矿业推动下的滇东北农业开发
第二节 清中期以降滇东北米价波动与驱动因素分析
第三节 人口压力下的高产作物种植
第五章 生计、聚落与文化:矿业开发与区域社会
第一节 生计、聚落:金沙江淘金与区域社会
第二节 群体记忆:金沙江淘金与淘金文化
第六章 矿业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变迁
第一节 金沙江滇西段淘金的生态影响
第二节 滇东北段矿业开发驱动下的区域环境变迁
结语
一、征服·共生:文明进程中的生态观
二、矿区生态链与景观生态研究
后记
内容摘录
结 语
金沙江流域因其复杂的气候和特殊的地理环境,呈现出地形多样、气候复杂、物产丰富、河流众多的自然环境分布格局,并造就了民族众多、宗教多元的人文环境特征,是一个集边疆安全、生态安全、多民族族际经济文化交流的整体性多功能富集区。环境史研究的本质是探讨人与环境的关系,涵盖人类对环境的认知、人与自然关系的定位、人类生产生活活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一门极具人文关怀的社会科学学科。本书以明清以来的金沙江矿业开发为切入点,选取金沙江滇西段和滇东段两个空间区域,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矿业开发与区域环境的互动,即地方政权的势力扩张、移民垦殖、粮食供应、人口格局乃至区域文化与区域环境的互动,去探寻区域生态变迁的内驱力和影响机制,呼应环境史研究之本质与内涵。
一、征服·共生:文明进程中的生态观
1962年,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描述出鸟儿消失、植物枯萎、鱼类死亡、农药危害等人类避而不谈却是真实的世界,开启了“现代环境运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人类以外的自然,发现环境问题揭开的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道道伤疤,自然因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自然的终结”“自然的死亡”“地球的危机”,而问题似乎出在人类社会为了满足自身的生存、发展需要不断去“征服”自然,人类征服欲望还在不断地延伸,从征服自然到征服另一个社会、另一种文化,一发不可收拾,无限制的征服带来的,是情况越来越糟,自然环境越来越糟糕,人类社会也只呈现着“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在“征服”欲下,毫无疑问,人类处于整个生态系统的中心,甚至,人类和自然生态系统被视作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这样的生态观几乎占据了此前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大部分时间,直至人类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的工业社会彻底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人类开始反思过去的生态观念。
我们在金沙江滇西段的矿产开发中看到,明清两季木氏土司打着守疆固边的名义,怀着攫取“他者”社会的自然资源的私心去开疆拓土,无疑是去征服一片陌生的自然区域、征服另一个社会、另一种文化;农民农闲间隙去淘洗砂金,也是征服自然维持其生存。说到征服,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往好了说,就是人类社会的经营开发,木氏土司在金沙江流域金矿开采,达到了维护边疆稳定、边疆社会发展的目的。因了掠夺攫取资源,木氏土司将其势力范围涉足到藏区,在新的征服区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组织,使原本械斗、纷争不断的边疆地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稳定。并推行移民实边,从腹里地区迁徙人口到荒无人烟之地,经营开发山区半山区,矿区形成新的人口聚居区,很多矿区今天仍是金沙江沿线主要的人口分布局、经济发展区。对于征服者——木氏土司、矿主、淘金者而言,创造了社会财富和经济价值,这无疑也是征服型资源开发产生的基本驱动力和直接收益。同时金矿开采促进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矿产开发带来人口的流动和迁徙。木氏土司采取的移民实边是规模较大、影响较大的一种途径,“三江口”俄亚大村就是因为金矿而发展壮大的,矿产开发的人口流动,也改变了地区的人口分布和民族分布。金沙江流域山陡谷深、地形险要,极大地阻碍了民族之间的交往,可通达性差,同一个南北走向的河谷与其他河谷地带的联系很少,“矿利”驱动却可最大限度地克服这些不利因素,促进人口、文化的区域性流动。征服也带来了不好的一面,而这种恶果在区域的自然生态系统上呈现得最为明显。人类为了一己私欲,无限制地攫取目力所及、足力可达、双手可取的一切自然资源,使自然生态环境遭受巨大变迁。一地的资源不能满足己欲,“硐老山空”便弃而不用,继续征服下一个目标。
人类的征服欲是无止境的,而自然生态系统却在维持着自身的能量守恒,一旦突破自然的临界值,便会遭受自然的反噬。金沙江流域历经历史时期的持续开发,引发一系列的水土流失、自然灾害便是一个个鲜活的例证,也唯有遭受反噬,人类感受到切肤之痛,才会发出旷野中那声呐喊,才会反观自身。人类社会就是经历了漫长的人口迁徙、经济交往、族际争端、资源共享、文化交流,才能明晰自身在地球历史中的“生态位”,一步步走向自然,走向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生态文明。
二、矿区生态链与景观生态研究
对于滇东北地区的矿业开发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传统史学基本都认为开矿对矿区及周围森林造成极大破坏,而清代滇东北铜矿产量居全国之首,消耗了大量木炭,森林的急剧减少引发了严重的灾害,东川至今仍是泥石流重灾区,本文中也阐述了这样的逻辑关系,即开矿—森林破坏—水土流失—环境灾害。最近,德国学者金兰中通过利用地理信息系统设计植被变迁模型,计算不同矿区森林破坏的面积,得出的结论却与传统史学观点有所不同,认为矿业确实严重地破坏了森林面积,但却不是森林消失的唯一原因,滇东北森林消失的原因是多元的,与农业垦殖及商业、柴薪需求等也有密切关系。笔者在写作过程中也认识到此问题,故而并非讨论滇东北地区矿业开采与环境变迁之间的直接对应关系,而是将矿业开发作为影响滇东北环境变迁的一个重要驱动因子,对矿业开发过程中所形成的人口移民以及之后的农业垦殖进行研究,这对更全面把握滇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革更为重要。而这种区域内的环境变迁驱动核心要素的对比上,可以发现东川与昭通有比较大的差异,东川府受矿业开采的直接影响大于昭通府,但昭通府却在人口大量进入、农业种植区域与规模都有极大改变后环境发生极大改变。因此,对金沙江滇东北段的矿业与环境变迁问题讨论也就需要具体问题深入分析,不可模糊区域内部之间的差异。
矿业、农业与人口交织推动,互为因果,共同推动了滇东北地区的经济、社会以及生态环境发展、变迁。滇东北地区由于地理环境的限制,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粮食主产区。境内水田有限,稻米生产基本能维持本地民食。清代康熙二十年以后,特别是雍正改土归流后,当地的农业垦殖速度加快;此外,该区域的矿业开发也进入黄金时期,人口大量涌入致使当地的粮食供给十分紧张。从乾隆元年以后的米价数据看,东川府的米价波动与矿业开发关系密切。矿业兴盛时米价也相应高昂;矿业走向低迷,米价则持续下滑,矿业开发是影响并主导东川府米价波动的主要因素。昭通府的米价则不同,其米价虽相对较高,波动也十分平稳。米价高主要是由于人口集中的城镇区(包括人口集中的矿业区)对稻米有刚性需求,而交通不便,将稻米需求量大的地区米价抬升;其米价波动平稳,仓储虽然有一定作用,但由于本地产米有限,仓储中稻米有限,故而仓储对当地稻米价格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在影响当地米价平稳的因素中,荞麦、玉米、马铃薯等杂粮种植对稻米市场的平衡作用十分关键。
清初期及之前的更长的历史时期里,滇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较好,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长时期以来,该区域也是内地所谓的“蛮夷”之地,保存着狩猎与农牧并存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内地移民进入开发后,滇东北地区的农业多元系统被打破,作物种植种类也逐渐向高产的作物转变,一些农作物的种植面积逐渐缩小,甚至是退出农业生产领域。野生动植物在逐渐减少或是消退了。虽然本文在精确考量滇东北农作物演变过程上仍有不足,但不可否认清代以后美洲高产作物的普遍种植及其对当地粮食结构调整的影响。美洲作物的广泛种植,不可避免地出现作物栽培的单一化趋势。斯科特(James.C.Scott)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中认为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具有“逃避作物”性质,它们为更多的人群逃避国家管控创造了条件。这种说法在云南地区虽仍有很大争议,但确实存在因美洲高产作物的种植,使得大量内地移民向山区深处推进的史实。作物的强适应性与相对高产,使移民群体的生存空间不断拓展,生存区域的地理海拔也不断被突破。森林、本土植物逐渐被美洲作物取代。在学界,对于作物单一化的负面影响一直有持续性的关注,诸如生态学、环境科学乃至环境史学者一直在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正如斯科特所言:“没有空闲土地的单一作物栽培比分散和混合的耕作更缺少环境恢复性(resilient)。它们更容易受作物疾病的影响;在作物歉收的时候,它们更缺少环境的缓冲;它们更容易导致专性虫害(obligate pests)的增加。”因粮食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化而形成的生态环境变革成为清代中期以后滇东北区域演变要素中的重要内容。当因粮食种植、矿业开采等原因引起的山地环境发生根本变化后,当地将出现新的生态连锁效应:水旱灾害频率也越来越短,范围越来越广;土壤侵蚀、地质灾害随之发生,诸如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频繁发生。灾害的发生又影响着农业的生产与粮食的产量,再次形成新的生态链。
生态变迁的外在呈现就是景观的变化。景观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前述森林植被与农业种植皆可视为自然景观;而人文景观则主要指随着人口进入该区域而人为营造的地域文化景观,诸如基于自然环境背景的东川十景的塑造等。从景观营造与族群关系角度再来认知滇东北的特殊地位,目前已有学者进行了尝试。黄菲的《重塑边疆景观:十八世纪的东川》(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 Dongchuan in 18th Century Southwest China)从王朝、地方、土著、移民等多个面向,展现在西南边疆的不同新旧人群互动下,交织而成的边疆景观塑造的历史过程,将汉人精英与矿业开发移民进入后,当地景观的再造过程逐渐揭开,但更多关注的是人文景观的塑造过程,诸如对青龙山真武祠与山泉溶洞的龙潭祭祀景观营造,文昌宫的构建所反映的空间争夺等。这种地方景观(人文景观)是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是文人精英遵循着特定艺文体裁,在不同族群互动及与本地景观的交叠中形成的。虽然人文景观作为考察边疆地区在中央控制与地方文化调和与互动上给了一个极佳的观察视角,但是,作为构成地表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地貌景观的变化以及所折射的生态变化过程,以及在自然景观变化过程中的人群生态,也是考察区域整体史的重要部分。或一定程度上说,揭示这种因生态要素变化而导致的地表景观变化,才是从根本上认知一个区域环境变迁轨迹的核心所在。
在地表景观变化因素中,人类改造、作用于环境所导致的自然灾害又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周边的地表景观。以泥石流灾害为例,虽然自然因素(包括降水、地表破碎程度及坡度等)是灾害形成的背景,但人类作用自然导致其生态系统完全改变,也是这种地质灾害形成的重要原因。泥石流是一种对人类和人类居住环境有严重危害的山地地质灾害,从灾害生态学的角度看,灾害也是一种景观塑造过程。金沙江南岸支流的小江流域是中国目前泥石流最典型地区,由于两岸岩层结构松散、植被稀疏,极易形成大规模巨大泥石流。每到洪水季节,泥石流来势凶猛,大大小小的石头被淤泥夹带着,伴随着粗粗细细的残枝断根形成巨大的“河流”,景象令人震撼。龙头山以下90千米范围内共有泥石流沟51条,其中以蒋家沟最为著名,蒋家沟泥石流流域内岩层破碎、地形陡峻、植被稀疏,灾害形式多样。通过对这种自然灾害塑造的地表景观的长时段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区域环境变化的驱动因素及后果。
目前将灾害与景观概念放在一起研究的,有美国学者对灾害与灾害事件与人文景观的塑造研究。从景观入手,探究美国社会对于灾难的态度和认知。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地表自然景观的塑造,目前还有诸多拓展空间。景观史研究在英国开始得较早,20世纪50年代霍斯金斯从长时段视角梳理了英格兰景观形成与演变的历史过程。一直以来,国内历史地理学也有研究景观的传统,但是在地理学的景观概念中,景观主要是指地表的覆被,包括自然覆被和人为覆被。自然覆被的变化研究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内容,不以景观概之,而是具体研究地理要素与人类活动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人为覆被则主要指人工建筑,包括城市、水利工程、大型防御工程(如长城等)等,主要是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内容,也较少以景观来统合历史时期的人为覆被构建。对景观、生态问题的研究,目前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学科:景观生态学。景观生态学概念是德国地理学者特罗尔,1968年特罗尔将景观生态学定义为对某一地域上生物群落与环境的、综合的、因果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温科(A.P.Vink)认为景观生态学是景观研究的一种方法,景观是维持自然生态系统和文化生态系统的;景观生态学研究生物圈、人类圈和地球表层或非生物组成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在史学研究领域,国内的历史地理以及环境史对景观生态学的相关研究方法、路径及成果的关注明显是不够的。在地理学的景观概念基础上,我们也吸纳了生态学的景观内涵,即景观不仅仅只是地表覆被,还是区域生态系统的某一特定时刻的稳定形式,将景观生态学介入对历史时期特定区域的环境变迁研究,是当前环境史研究的最新尝试,这种尝试将景观视为地表生态系统,从整个生态系统与地表景观的形成角度认知区域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
当前景观史与环境史已经有交叉,虽然二者有区别,但环境史研究仍有诸多可以借鉴景观史之处。高岱认为景观史与环境史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即人类活动与客观存在的联系问题,但二者研究的重心与落脚地还是有所不同,景观史更多关注的是人类活动与山川地貌之间的联系,这些“山川地貌”基本上是在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内,而环境史研究所关注的“环境”已超出地理学的范围,涉及诸如气象学、生态学等更多学科。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环境史研究在理论与路径上有着先天的缺陷,即不自觉地进入古今环境对比的套路之中,由此而延伸出此前环境史研究中已经被学者们认识到并逐步摈弃的“破坏论”。而景观史的研究更多只是关注不同历史时期景观的变化过程,这个变化过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都是不同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一个面相。笔者在对滇东北地区的环境变迁研究中,以矿业开发为导线,进而分析当地矿业移民、农业种植与生态环境变迁之间的关系,其本质上是希望揭示长时段区域生态演变的内在驱动力及其后果。这种综合性的考察,特别适合从景观角度展开,然而,限于能力与时间,书中未能得到系统呈现,加之本文乃硕士毕业论文基础上进行的修改,虽已做出改动,但限于当时学识与认知,对许多问题的把握不到位,而在此提出之关于未来研究设想,也只能留待他日。不过,笔者相信,从景观角度系统审视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变迁必是未来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