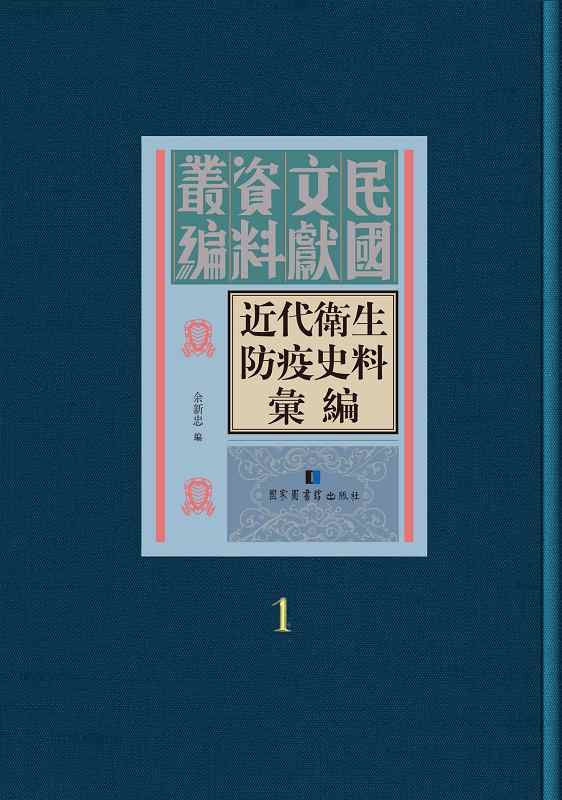
图书封面
书名:近代卫生防疫史料汇编(全五十册)
编著者:余新忠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12-31
ISBN:978-7-5013-7127-3
作者简介:
余新忠,浙江临安人,1991年本科毕业于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2000年),日本京都大学博士后(2005年)。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职。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百千人人才工程等人才项目,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持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宋元以来中医知识的演进与现代中医的形成研究”。主要从事医疗社会文化史和明清社会史研究。著有《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等著作4部,另有编著、译著7部,在《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東洋史研究》(日本)、《近代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中英日文论文90余篇。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获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2),《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2015),另有成果获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二等奖各一项和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两项、二等奖一项,高等教育天津市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一项(主持人)。
读者对象:
内容简介:面对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本书选编近代以来我国重要的卫生防疫资料,为公共卫生防控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内容包括:一卫生行政,即卫生署及各省市地方卫生局、民政厅的工作报告、简报、工作计划及颁布的法令法规等;二卫生防疫,收录中央及各省市防疫处、海港检疫处的报告、管理规程;三防疫附属机构资料,包括时疫医院、传染病医院的报告,医学研究会的会议记录、会议报告;四防疫宣传,收录新闻局等官方及民间机构所编传染病常识的宣传册;五防疫期刊,收录中央防疫处、华北防疫委员会、卫生署东南鼠疫防治处等编期刊。这些史料反映近代卫生防疫的发展脉络,国家与社会在应对疫情预防与治理时的运行机制,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提供参考。
目录:總 目 録
第一册
全國防疫計畫書 國民政府內政部編 國民政府內政部,一九二八年出版 一
中央防疫處一覽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二六年出版 一九
中央防疫處十二周年刊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三一年出版 一〇三
中央防疫處民國二十、廿一年度報告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三三年出版 二六七
中央防疫處二十八年度工作報 告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三九年出版 三六九
中央防疫處三十四年工作報告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四六年出版 三九五
防疫彙報(二十八年度) (僞)中央防疫委員會編 (僞)中央防疫委員會,一九四○年出版 四三三
第二册
防疫彙報(三十年度) (僞)華北防疫委員會編 (僞)華北防疫委員會,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
辦理綏遠臨時防疫經過彙編衛生部編衛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四五
徐州防疫委員會工作報告 江蘇省立徐州民衆教育館編 江蘇省立徐州民衆教育館,一九三二年出版 三一三
福建省會衛生防疫委員會報告書(第一期) 福建省會公安局衛生防疫會 編福建省會公安局
衛生防疫會,一九三三年出版 三七一
福建省立衛生試驗所五周年紀念刊 福建省立衛生試驗所編 福建省立衛生試驗所,一九四一年出版 四九一
第三册
福建省地方病情形與防治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編 福建省政府秘書處,一九三九年出版 一
江西省會防疫報告書(民國二十一年份) 江西省會臨時防疫委員會編 江西省會臨時防疫委員會,一九三三年出版 四九
廣州市衛生行政之檢討 鄧真德編著 廣州市政府衛生局,一九三五年出版 二五一
京漢鐵路防疫始末記 李遂賢編 京漢鐵路管理局,民國間出版 三三七
衛生會議彙刊(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衛生部編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北軍區衛生部,一九四八年出版 三七五
第四册
衛生員講義 蘭溪實驗縣衛生行政管理處編 蘭溪實驗縣衛生行政管理處,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日用衛生 孫佐編;嚴保誠校 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年出版 七一
隔離醫院護病須知 鍾志和編 杭州廣濟醫刊社,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八三
公共衛生 衛楚材著 亞細亞書局,一九三五年出版 二五七
公共衛生實施概要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六年出版 四三七
水與疾病 內政部衛生署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 四五七
第五册
飲水衛生及其他(教育電影劇本故事集) 陳果夫編著 國立編譯館,一九四七年出版 一
防疫概要 祝紹煌等編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三年出版 一九五
防疫須知 顧鳴盛編 文明書局,一九二四年出版 二六一
防疫工作手册 東北防疫委員會編 遼寧省政府,一九四七年出版 三三三
增訂瘟疫明辨上 (清)鄭奠一撰 大東書局,一九三七年出版 三六一
增訂瘟疫明辨下 (清)鄭奠一撰 大東書局,一九三七年出版 四四五
第六册
瘟疫論上 (清)戴天章撰 大東書局,一九三七年出版 一
瘟疫論下 (清)戴天章撰 大東書局,一九三七年出版 七五
傳染病 余雲岫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二〇年出版 一四七
學校家庭傳染病預防消毒及救急療法 郭人驥編 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出版 二〇一
怎樣預防傳染病 程文彬編輯 世界書局,一九四二年出版 三七五
慢性傳染病概要 一九四三年出版 四〇三
急性傳染病概要 一九四三年出版 四三一
夏天的傳染病 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編 東北書店,一九四八年出版 四六三
第七册
傳染病預防工作指南 陳述譯 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出版 一
預防傳染病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編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民國間出版 一六一
滅虱治疥站工作須知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七五
天花 王光宇著 湘雅醫科大學,一九二九年出版 二三七
天花 衛生署醫療防疫隊編 衛生署醫療防疫隊,一九四〇年出版 二六七
預防天花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民國間出版 二八七
撲滅天花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衛生局編 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共衛生局,一九四九年出版 三一七
種牛痘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編 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會,民國間出版 三二九
黑熱病 山東省膠東區行政公署衛生局編 山東省膠東區行政公署衛生局,一九四九年出版 三四七
肺癆病救護法 丁福保譯 醫學書局,一九一一年出版 三九七
第八册
癆病 胡宣明編 中華衛生教育會,一九二一年出版 一
一致抗癆 中國防癆協會編 中國防癆協會,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七
抗癆 劉德啓等著 抗癆出版部,一九四一年出版 三三
杭州之瘧疾 洪式閭著 一九三一年出版 二〇三
蚊與疾病 內政部衛生署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 二五七
瘧疾 內政部衛生署醫療防疫隊編 內政部衛生署醫療防疫隊,一九四〇年出版 二八一
瘧疾的爲害及其防止(漢藏文對照)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編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一九四一年出版 三〇九
瘧疾概要 錢沛澤編著;周綸校 中華醫藥服務社,一九四四年出版 三五三
第九册
瘧疾及其預防 趙慰先,金錦仁編著正中書局,一九四六年出版 一
抗瘧教育 周尚著 商務印書館,一九四七年出版 一〇一
鼠疫 譚其濂 編商務印書館,一九一六年出版 三三七
第十册
寄寄山房鼠疫雜誌 一九一一年出版 一
鼠疫預防須知 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編 新華書店,一九四九年出版 二二五
福建龍岩鼠疫及環境衛生調查初步報告 楊永年、蘭度雅著 民國間出版 二五五
霍亂及其預防方法 內政部衛生署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 二七一
瘟疫霍亂答問 霍亂審證舉要 (清)陳蟄廬撰;(清)連文冲述;章瑜校對大東書局,一九三六年出版 二九九
民國二十八年北京特别市霍亂預防工作簡報 (僞)北京特别市公署衛生局編 (僞)北京特别市公署衛生局,一九三九年出版 三九三
北碚霍亂防治經過報告 北碚管理局衛生院、江蘇醫學院附設公共衛生事務所合編 北碚管理局衛生院、江蘇醫學院附設公共衛生事務所,一九四二年出版 四九五
花柳病及其預防方法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編 蒙藏委員會編譯室,一九三一年出版 五一九
第十一册
三個窩子病 東北行政委員會衛生部編 東北書店,一九四八年出版 一
腦膜炎及其預防方法 內政部衛生署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 二九
傷寒及其預防方法 內政部衛生署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 四一
白喉及其預防方法 內政部衛生署編 行政院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 六五
禿瘡 內政部衛生署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二年出版八 一
梅縣籌辦平民醫院委員會概况 民國間出版 九七
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徴信録 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編 中國紅十字會時疫醫院,一九一六年出版 二六七
第十二册
上海時疫醫院十七年報告兼徴信録 上海時疫醫院編 上海時疫醫院,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
上海時疫醫院二十年報告兼徴信録 上海時疫醫院編 上海時疫醫院,一九三二年出版 二四三
第十三册
上海時疫醫院廿三年報告兼徴信録 上海時疫醫院編 上海時疫醫院,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
上海時疫醫院廿四年報告兼徴信録 上海時疫醫院編 上海時疫醫院,一九三五年出版 二二九
第十四册
上海時疫醫院廿五年報告兼徴信録 上海時疫醫院編 上海時疫醫院,一九三七年出版 一
集義善會虹口時疫醫院二十一年報告兼徴信録 集義善會虹口時疫醫院編 集義善會虹口時疫醫院,一九三二年出版 二三五
第十五册
上海急救時疫醫院工作報告 急救時疫醫院事務處編 急救時疫醫院事務處,一九四〇年出版 一
國立同濟大學醫科研究所細菌學部工作報告 國立同濟大學醫科研究所細菌學部編 國立同濟大學醫科研究所細菌學部,一九四四年出版 一二五
莫干山肺病療養院章程 莫干山肺病療養院編 莫干山肺病療養院,一九二八年出版 一五七
國立湘雅醫學院要覽 國立湘雅醫學院編 國立湘雅醫學院,一九四二年出版 一九七
湖南省立傳染病醫院周年工作報告 湖南省立傳染病醫院編 湖南省立傳染病醫院,一九三七年出版 二七九
薩克生血清廠良藥彙刊 薩克生血清廠編 薩克生血清廠,民國間出版 三〇五
第十六册
通俗衛生月刊 第一期—第二期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二二年出版 一
衛生雜誌 第一卷第一號—第一卷第四號 中央防疫處編 中央防疫處,一九二五年出版 一四九
衛生公報 第一卷第一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二三七
第十七册
衛生公報 第一卷第二期—第一卷第四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
第十八册
衛生公報 第一卷第五期—第一卷第七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
第十九册
衛生公報 第一卷第八期—第一卷第九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
第二十册
衛生公報 第一卷第十期—第一卷第十二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
第二十一册
衛生公報 第二卷第一期—第二卷第一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
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第二十二册
衛生公報 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卷第四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
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第二十三册
衛生公報 第二卷第五期—第二卷第六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
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第二十四册
衛生公報 第二卷第七期—第二卷第九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
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第二十五册
衛生公報 第二卷第十期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編 國民政府行政院衛生部,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中國衛生雜誌 第一期—第七期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編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一九二九年出版 一四七
第二十六册
中國衛生雜誌 第八期,第十二期,第十七期—第二十一期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編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第二十七册
中國衛生雜誌 第二十二期—第三十期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編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一九三〇年出版 一
第二十八册
中國衛生雜誌 第三十一期—第三十四期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編 《中國衛生雜誌》編輯部,一九三〇—一九三二年出版 一
衛生半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四期 內政部衛生署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衛生
教育系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四年出版一七九
第二十九册
衛生半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第一卷第十期 內政部衛生署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衛生
教育系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
第三十册
衛生半月刊 第一卷第十一期—第二卷第五期 內政部衛生署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衛生教育系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
第三十一册
衛生半月刊 第二卷第六期—第二卷第十二期 內政部衛生署全國經濟委員會衛生實驗處衛生教育系編 內政部衛生署,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
第三十二册
公共衛生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四期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
第三十三册
公共衛生月刊 第一卷第五期—第一卷第九期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第三十四册
公共衛生月刊 第一卷第十期—第二卷第二期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第三十五册
公共衛生月刊 第二卷第三期—第二卷第七期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出版 一
第三十六册
公共衛生月刊 第二卷第八期—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 衛生署編 衛生署,一九三七—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
第三十七册
華北防疫委員會工作季刊 第六期—第十期 (僞)華北防疫委員會常務委員室編 (僞)華北防疫委員會常務委員室,一九四〇—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
第三十八册
華北防疫委員會工作季刊 第十一期—第十二期 (僞)華北防疫委員會常務委員室編 (僞)華北防疫委員會常務委員室,一九四一年出版 一
衛生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六期 北平市政府衛生局編 北平市政府衛生局,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七三
第三十九册
衛生月刊 第一卷第八、九期合刊—清潔掃除運動專號 北平市政府衛生局編 北平市政府衛生局,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廣西衛生旬刊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四期 廣西梧州醫院編 廣西梧州醫院,一九三三年出版 三九三
第四十册
廣西衛生旬刊 第一卷第五期—第一卷第二十五期 廣西梧州醫院編 廣西梧州醫院,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出版第一卷第五期 一
第四十一册
廣西衛生旬刊 第一卷第二十六期—第二卷第五期 廣西梧州醫院編 廣西梧州醫院,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
第四十二册
廣西衛生旬刊 第二卷第六期—第二卷第二十三期 廣西梧州醫院編 廣西梧州醫院,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
第四十三册
廣西衛生旬刊 第二卷第二十四期—第三卷第六期 廣西梧州醫院編 廣西梧州醫院,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
第四十四册
廣西衛生半月刊 第三卷第七期—第三卷第十六期 廣西梧州醫院編廣 西梧州醫院,一九三五—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百色衛生 廣西百色衛生區衛生事務所,廣西百色衛生區省立醫院編 廣西百色衛生區衛生
事務所,廣西百色衛生區省立醫院,一九四〇年出版第一、二期合刊 二四一
貴州衛生 創刊號—第七至十二期合刊 貴州省衛生處衛生月刊編輯委員會編 貴州省衛生處衛生月刊編輯委員會,一九四二年出版 二五七
第四十五册
醫防通訊 第一期—第三期 內政部衛生署醫療防疫隊總隊部編 內政部衛生署醫療防疫隊總隊部,一九三九年出版 一
防癆 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卷第七期 中國防癆協會編 中國防癆協會,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出版 三三
第四十六册
防癆 第一卷第八期—第二卷第四期 中國防癆協會編 中國防癆協會,一九三六年出版 一
第四十七册
防癆第二卷第五期—第二卷第六期中國防癆協會編中國防癆協會,一九三四— 一九三五年出版 一
工業衛生通訊 創刊號—第六期 上海工廠聯合醫務處編 上海工廠聯合醫務處,一九四四年出版 一五三
旅行衛生 第一期—第二期 上海海港檢疫所編 上海海港檢疫所,一九四七年出版 三二五
第四十八册
廣東抗虐 第一期—第三期 廣東省政府衛生處編 廣東省政府衛生處,一九四五—一九四六年出版 一
東南鼠疫防治簡報 衛生署東南鼠防治處編 衛生署東南鼠防治處,一九四八年出版第二卷 第二期 七三
社會衛生 創刊號—第一卷第七期,第二卷第三期 社會衛生月刊社編 社會衛生月刊社, 一九四四—一九四六年出版 八三
第四十九册
社會衛生 第二卷第四期—第二卷第十期 社會衛生月刊社編 社會衛生月刊社,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出版 一
恩光新醫學雜誌 第一期—第六期 恩光新醫學雜志編 恩光新醫學雜志,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出版 二四三
第五十册
戰時內務行政應用統計專刊(衛生統計) 內政部編 內政部,一九三八年出版 一
健康教育(中華兒童教育社會刊) 中國兒童教育社編 大東書局,一九三四年出版 一三五
前言:瘟疫與人:中國的經驗及其歷史啓示
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以“微寄生”和“巨寄生”兩個概念來認識人類生命的生存狀態,認爲,“人類大多數的生命其實處在一種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敵的巨寄生構成的脆弱的平衡體系之中,而所謂人類的巨寄生則主要是指同類中的其他人。” (美)威廉·麥克尼爾著;余新忠、畢會成譯:《瘟疫與人》,中信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第六頁。由致病微生物引發的瘟疫,無疑是人類所處的微寄生關係的重要表現形式,藉由微寄生乃至疫病,人類與自然的勾連變得更加的細密而深廣。不僅如此,在作爲展現人與國家關係的巨寄生體系中,瘟疫的影響也從未缺席,不僅自古就與饑荒、戰争一道成爲影響人類規模擴張的三大敵人,而且也因此成爲了影響人類文明機制和歷史進程的重要的自然性力量。由是觀之,在人類的歷史上,瘟疫實際上站在了人與自然、個人和社會與國家等諸多關係的鏈結點上。
瘟疫無疑是人類的灾難,但也往往是歷史的推手。處於諸多鏈結點上的瘟疫,在給人類生命健康帶來諸多傷害的同時,也對人類社會自身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警示。顯然,瘟疫作爲一種無可避免的歷史現象,對於人類歷史的影響并非全然的是負面,實際上,很多人類科技進步、生活設施的改進、制度建設乃至人與自然關係的調整等等,都與瘟疫的刺激有直接的關係。同樣顯而易見的是,瘟疫本身并不會獨立産生意義,其發揮的歷史推動作用,無疑有賴人類的理性和反省批評精神。
無論是歷史還是現實,都在顯示,瘟疫不衹是天灾,也是人禍,天灾或不可控,人禍總應努力避免。而要避免重蹈覆轍,反省和批判無疑是最好的武器。而對反省和批評來説,若不能立足歷史來展開,必然就會缺乏深度和力度。由是觀之,包括瘟疫史在內的疾病史研究,無論對於我們認識歷史還是理解現實,以及更好地面向未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不過,對於歷史的探究和省思,似乎很難給人某種直接的行動指南,可能也無助於直接推動科學的發現和技術的進步。哲學家陳來教授曾在反思SARS事件時指出:“人文學科在整體上對於社會的意義,本來也不在於對於某種突發的自然灾疫提供直接的對策,而在於在學術研究的同時,長遠地促進社會的進步、價值的穩定、文化的發展、精神的提升。” 陳來:《非典引發的哲學和文化反思》,《群言》二〇〇三年第八期。故而,從歷史的梳理和討論中,我們可以獲得的,可能主要是通過拓展視野、轉换立場,以及發現豐富多元的信息、人類智慧複雜的表達和人類核心價值的共通性來啓迪我們的思維,可以讓我們在更高的層次上省思現實的存在和前進的方向,不至於衹是低頭拉犁,而不抬頭看路。於此,我們不妨從對中國歷史上的疫病及其社會應對入手,通過梳理這一段歷史,看看究竟可以從中得到怎樣的歷史啓示。
一、中國歷史上的重大疫情及其特點
疫的意涵,按《説文解字》的解釋,是“民皆疾也”。意謂有如徭役之役,“衆人均等”之意。故就疫之本義而言,是指流行病,不過由於古代的流行病一般都是傳染病,所以瘟疫也多被視爲具有較强傳染性和危害性的傳染性疾病 參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三年,第四—九頁,下同。。早在殷商時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禍風”“癘”和“役”這樣的記載。此後史不絶書,時有加增。如果僅從現存的歷史記載來看,中國歷史上疫病的發生頻率整體上一直呈上升態勢 現有幾種具有歷史連續性統計均反映了這樣的趨勢,參閱張泰山:《民國時期的傳染病與社會——以傳染病防治與公共衛生爲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十二—三十三頁。。從現有一般截止到一九四九年的統計看,民國時期的瘟疫發生頻度是最高的。於此,我們不妨將目前有關歷代瘟疫頻次的統計圖表羅列於下:
資料來源:張志斌:《中國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福建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七年,第一百二十二頁。
資料來源:李文波編著:《中國傳染病史料》,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二〇一二年內部印行本。
資料來源:龔勝生:《中國疫灾的時空分布變遷規律》,《地理學報》二〇〇三年第六期。
上述圖表雖然統計的資料有所不同,但均顯示,隨著時間的推移,瘟疫發生的次數和頻次整體上均呈明顯上升之態勢,其中明清以後,特别是到民國時期,增量顯著。這種現象的出現,固然與近世以來,人口劇增和社會流動日漸頻繁以及日趨國際化等因素爲疫病發生與傳播帶來的便利這樣的原因有關 可參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三百四十—三百四十六頁。,但更爲重要的,恐怕還是因爲資料保持的完整程度與社會對這類記載的關注程度不同造成的。而且,上面統計均以整個中國作爲空間單位,一方面資料必然存在遺漏,另一方面每次瘟疫很多是局部的,即使全國性的,并不表示延及全國每個地方,所以這類統計資料衹能反映中國歷史上瘟疫發生的概貌和趨勢。
通過上述對中國瘟疫歷史概覽式的梳理以及相關具體的研究,我們認爲中國歷史上的瘟疫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疫灾的發生具有比較明顯的周期性。雖然自古以來,瘟疫的頻次整體上呈日趨升高的態勢,但顯然不是均匀地呈直綫式上升的,而是表現爲在某一段時間相對多發。在二十世紀之前,公元二〇〇年前後的東漢末魏晋時期、十三世紀初的宋金時期、一六〇〇年前後的晚明時期和十九世紀,是四個比較明顯的瘟疫相對高發時期。
第二,整體上瘟疫頻次和瘟疫的種類的不斷增加,表明人口和社會經濟的發展,對於瘟疫流行來説是個“雙刃劍”。雖然這種增高受歷史記載豐富程度和史料保存情况等因素的影響,但從比較晚近的歷史,比如晚清以降的情况來看,這種趨勢大體也是成立的。不僅如此,現有的研究也表明,瘟疫的種類也在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多,現代更是如此。究其原因就在於,雖然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助於社會提升應對疫病的能力,但其帶來的人口的增長、人們活動範圍的擴大和社會流動性增强等,不僅大大增加疫病發生和傳播的幾率,還由於人類進入新的自然空間而引發新疫病的機會也在增多。不過另一方面也應該看到,至少從比較晚近以來,雖然瘟疫的頻次大大增多,但對人口的損傷等直接的危害則相對减弱。
第三,重大疫情往往發生在時局動盪或社會格局發生重大轉變之時。從上述關於重大疫情的概述中,明顯可以看到大疫往往發生在王朝末期。這在直觀上似乎令人感到瘟疫對於王朝的覆亡具有重大影響,但實際上,瘟疫不同于水旱等自然灾害,若救濟不當,很容易引起民變,從而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正常情况下,瘟疫反而會抑制民衆的群體性活動。瘟疫的發生,雖然不可避免會對國家的統治造成一定的影響,但重大疫情較多出現在王朝末期,主要可以説明的還是,政治的腐敗、時局的動盪、戰争的頻仍等王朝末期常常出現的情形,對於瘟疫流傳往往具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故而容易釀成大疫。而整體的社會格局即將發生重大變化時,也往往容易出現大疫,這比較明顯地體現在嘉道之際的霍亂大流行上。當時,中國社會正處於被逐步整合到以西方爲主導的全球貿易格局之中,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源於印度恒河流域的真性霍亂在一系列機緣巧合中走出印度,引發了全球性的霍亂大流行,中國也未能幸免,不僅遭遇了一次非常嚴重的全國性大疫,而且霍亂從此留在了中國,不時肆虐,對中國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參閱余新忠:《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二期。。
第四,瘟疫引發的危害不衹是源於病原體本身,而且很多情况下,還來自於由此引發的社會恐慌和無序應對。筆者在對中國明清以來瘟疫的研究中發現,瘟疫對社會的直接破壞和影響,并不像目前一些初步研究所揭示的那麽大,其更重要的影響還在於造成民衆的莫名恐惧和信心流失,引發社會恐慌。這種恐慌不僅容易造成諸多無序而有害的應對,比如盲目地逃離、聚衆舉辦祈禳活動等,對社會秩序和經濟生活等造成破壞,而且還可能帶來諸如以鄰爲壑、對染病親人弃之不顧等人倫和道德危機。這種危機,除了當時直接明顯的危害外,還可能對人們心態和風俗信仰方面産生相對隱性而深遠的影響,非常值得重視。
二、中國重大疫情及其應對舉隅
爲了使我們比較直觀地理解歷代瘟疫與社會應對及其影響,我們不妨選擇其中主要在危害嚴重程度、疫情特點及其對後世影響等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十大瘟疫,做一概述:
(一)東漢末年大疫。東漢末年,政局動盪,饑荒頻仍,瘟疫繼起。在建安元年(一九六)後的二三十年中,瘟疫幾乎連年不斷,甚至有“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大疫加上連年的兵荒馬亂,致使當時出現了“千里無雞鳴,白骨露於野”凄慘局面。這次大疫造成的死傷難以估算,不過至少帶來了以下兩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是直接促成了對中國醫學具有根本性影響的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的誕生;二是對於佛教引入和流行以及道教的興起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二)南朝宋齊間瘟疫。從劉宋元徽四年(四七六)起,至蕭齊建武年間(四九四—四九七),南方的湖南、浙江等地多次發生瘟疫,“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戴白漿”的“虜瘡”(即天花)通過戰争,從南方傳入中原。此後,遍行于中國大江南北,成爲中國歷史上對民衆生命與健康最具影響力的烈性傳染病。
(三)北宋元祐瘟疫。宋哲宗元祐年間(一〇八六—一〇九四),饑荒時現,瘟疫無年不有,特别是在黄淮、兩浙地區尤甚。饑荒加瘟疫,給民衆的生命和健康帶來極大的破壞,死亡甚衆。面對灾疫,當時一些官員的應對頗具亮點。元年(一〇八六),淮南、京東等地大旱,饑民流亡載道,龍圖閣學士滕元發爲防止饑民中的瘟疫爆發并帶至京城,召集城中富民捐資,快速在城外的廢營地,搭建蘆葦、竹篾、茅草等臨時住所兩千五百間,井、灶、器用皆備,保全灾民五萬多。四年(一〇八九),杭州大旱,饑疫并作,時任杭州知州蘇軾,爲救治疫病,捐廉以倡,共募集資金黄金五十兩、錢兩千緡,創建了專門用來安置和治療病人的病坊,名之安樂坊。
(四)金末汴京大疫。金哀宗正大九年(一二三二)初,金兵與蒙古軍交戰,金主力被殲,蒙古鐵騎兵臨當時金朝首都汴京城下。金朝則將城外軍民悉數遷入城內,閉城死守。經過十六晝夜的頑强抵抗,最終逼退了蒙古軍隊。四月初,汴京成功解圍,金朝改元天興以示慶賀。然而還没來得及歡慶,另一場更大的灾難便接踵而至了。解圍之後,城裏瘟疫爆發,“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據今人研究,當時城內人數約二百餘萬,而死者達百萬以上,可謂慘烈無比。這次大疫,極大地打擊了金朝的士氣和實力,加速了其滅亡。當時身在疫區的“金元四大家”之一李杲主要依據這次瘟疫的治療經驗,完成了名著《內外傷辨惑論》。
(五)元末北京大疫。元朝末年,朝政腐敗,各地農民起義風起雲湧,至正十五年(一三五五)以後,隨著南方的起義隊伍力量日漸壯大,大量難民開始流亡京師。至正十八年(一五五八),聚集了數十萬難民的京師,出現疾疫,并在難民中迅速傳播,一時死者枕藉。大量死尸暴露野外,給疫病進一步的傳播帶來極大的風險。當時最受元順帝寵信的宦官朴不花(高麗人)爲了博取名聲,主動請纓,張羅埋葬事宜,獲得順帝支持後,出錢出力,在一年多的時間裏,收葬尸體二十萬具。
(六)明末崇禎大疫。明朝末年,朝政混亂,內外交困。繼明末萬曆年間的兩次大疫後,崇禎六年(一六三三)又迎來了明朝最後也是最嚴重的一次大疫,這次大疫首先出現於山西,而後伴隨著流民和戰亂,逐步由北向南、由東向西傳遍大江南北。至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達到高潮。這次大疫,不僅持續時間較長,更突出的是病情凶險,令人驚駭不已。比如一六四三年傳到北京後,“京城內外,病稱疙瘩,貴賤長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據推測,極有可能是肺鼠疫。當年僅京城疫死者就達二十餘萬,全國死亡人數當在百萬以上。其對於明朝的滅亡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而正是在這一時期,吴有性撰寫了著名的《瘟疫論》。
(七)嘉道之際霍亂大流行。清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數年前在印度爆發的霍亂,最終通過海上的商貿船隻,在東南沿海登陸,并於第二年迅速通過水陸交通要道,特别是長江和運河傳遍全國大部地區。這是真性霍亂首次傳入中國,由於傳染性强,病死率高,時人又缺乏認識和適切的應對,引起了社會的極大恐慌。人人恐懼,訛言四起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爲豐都地獄,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經”。這次大疫三四年後纔逐漸平息,但霍亂從此留在了中國,不時肆虐。這次大疫是世界性霍亂大流行的一部分,中國并没有像西方那樣,因此而促進了公共衛生事業的起步,但也推動了醫學上的進步。
(八)一八九四年粵港腺鼠疫大流行。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年)三月,廣州出現了腺鼠疫疫情,并於五月傳至香港,隨後疫情日熾,至八月逐步平息。這次鼠疫在廣州導致四萬餘人死亡,而在香港確認死亡人數爲兩千五百五十二人。在這場鼠疫中,圍繞著疫病的防控,中西方發生了極大的衝突,港英當局利用這次機會,强力推行西方的清潔、檢疫等防疫舉措,過程中雖有妥協,但最終還是推動了衛生行政的發展。而華人精英則通過創設東華醫院來爲華人和中醫争取到了一定的權利。不僅如此,國際醫學專家的介入,還使得鼠疫桿菌首次被成功分離。
(九)清末東北鼠疫流行。宣統二年(一九一〇)九月,一種可怕的鼠疫——肺鼠疫開始出現在中俄邊境城市滿洲里,迅速蔓延東北三省其他地區并波及關內的直隸以及山東、河南諸省,直至次年三月纔逐漸平息,六萬餘人因此死於非命。面對瘟疫,迫於外國殖民勢力的干涉,清政府邀請英國劍橋醫學博士、馬來亞華人伍連德主持防疫事務,他積極引入西方先進的防疫機制,采取清潔、檢疫、隔離和尸體焚燒等舉措,最終撲滅了疫情。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正式引入近代衛生防疫機制開展大規模的疫病防控,極大地推動了中國近代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
(十)一九三二年全國性霍亂大流行。一九三二年四月,霍亂首先出現於武漢、上海等地,而後逐步向各地蔓延,特别是到六月後,陝西開始出現疫情,疫情快速發展,破壞程度觸目驚心,波及除東北以外的絶大多數省份,死亡人數僅陝西就達二十萬以上,全國則至少有五十萬,是民國期間影響最廣、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瘟疫。針對這一瘟疫,南京國民政府利用初步建立的衛生防疫體系進行防控,但在防控中,農村醫療衛生設施的薄弱暴露無遺,既極大地影響了防控效果,也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時國家的公共衛生建設。
三、中國歷代疫情應對的舉措與特點
人們應對瘟疫的舉措,大體不外乎衛生賑濟等應急舉措和醫療。而前者又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灾疫發生後,人們直接的應對舉措;另一類則爲日常的預防措施和衛生習俗。關於前者,從國家的角度來説,雖然傳統時期,國家對待瘟疫一直没有像對待水旱蝗等其他灾害那樣,在疫病救療上,做出具體而細緻的制度性規定,但每當發生疫情,無論是朝廷和地方官府,往往都會采取一定的舉措。比如西漢平帝元始二年(二),各地發生嚴重的蝗灾,青州尤其嚴重,由蝗灾而次生瘟疫,官府“舍空邸第,爲置醫藥”,并向死者發放殯葬費 (東漢)班固:《漢書》卷十二《平帝紀》,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第一册,第三百五十三頁。。唐代文宗大和六年(八三二),南方發生水旱之灾,繼以疾疫,唐文宗專門下“拯恤疾疫詔”,稱:“自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己,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恤。”并要求,“其疫未定處,并委長吏差官巡撫,量給醫藥,詢問救療之術,各加拯濟” (清)董誥:《全唐文》卷七十二,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第七百五十三頁。。綜合起來,古代朝廷和官府采取的舉措主要有:設(醫)局延醫診治、制送成藥、建醮祈禳、刊布和施送醫方、掩埋尸體、設置留養和隔離病人的場所和局部的檢疫隔離等。
國家層面缺乏對瘟疫救療具體而明確的制度性規定,這固然跟瘟疫不像其他自然灾害,比較容易直接引發民變有關,但同時也與疫病救治的複雜性是分不開的。在當時的社會醫療條件下,官方實際上難以全面擔負起複雜的疫病防治責任。一方面,官辦醫療機構效率和能力有限,不可能滿足民間疾疫救治的實際需求。另一方面,瘟疫的救療在技術上要比饑寒的賑濟複雜得多,不僅存在著疫情千變萬化和病人個體性差异等複雜性,而且古代醫療資源存在著很大的地區不平衡性,而當時的朝廷也難以具備進行跨區域調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醫治療講究陰陽、寒熱、虛實、表裏,若不能對症施藥,可能會適得其反。這樣,與其作統一的規定,反而不如聽任地方社會相機行事。在這種情况下,國家往往多會宣導和鼓勵民間社會力量來承擔瘟疫的防治任務,特别是明清時期,利用了日漸興起的民間社會力量(比如鄉賢),促使其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借助比較豐富的地方醫療資源和日漸興盛的慈善力量和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疫病救療活動。其舉措主要包括:施送醫藥、刊刻散發醫方、懇請官府開展救療、建立留養所等收治病人、利用宗族義莊或行業公所等組織開展制度化的救治和創設醫藥局等專門的慈善機構進行疫病救治等。而就個人而言,面對瘟疫直接的應對往往還有閉門不出或逃離疫區以及焚香或焚燒蒼術、白芷等藥物以驅避疫氣等 以上參閱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廣西科學技術出版社,二〇〇六年,第三十—三十五、五十二—六十、九十二—一百零五、一百四十—一百四十九頁;張劍光:《三千年疫情》,江西高校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二十—二十五、三十四—三十八、一百三十三—一百四十四、二百零三—二百一十四、二百五十六—二百六十一、三百二十一—三百二十九、四百三十一—四千四百四十一頁;韓毅:《宋代瘟疫的流行與防治》,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五年,第一百三十四—二百三十四、四百零九—五百二十五頁;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二百一十九—二百五十三頁。
而關於日常的預防舉措和衛生習俗,中國社會積纍了頗爲豐富的經驗。很早就出現了“治未病”的思想,其雖然不能和今日的預防醫學相提并論,但對於維護個人健康多少是有利的。而且長期形成的諸多節日風俗,很多都與衛生避疫有關,比如端午節的熏燒蒼術等藥物、飲用和噴灑雄黄酒,重陽節的登高等等。另外還有清潔環境、勤沐浴等以保持個人衛生、驅避蚊蠅、强調生活有節以保持正氣充盈、提倡飲用開水和食用蔥蒜以防疫氣等有利於衛生的習俗。參閱范行准:《中國預防醫學思想史》,華東醫務生活社,一九五三年,第十四—八十一、一百—一百三十三頁;拙著:《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一百六十三、二百一十九頁。
除了在應對疫病方面積纍頗爲豐富的經驗和舉措之外,中國醫學在對疫病的治療上,也有令人矚目的成績。雖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醫往往以治療慢性病和身體調養見長,但實際上,對“傷寒”“溫病”等感染性疾病的認識和治療,乃是中國傳統醫學最重要的特長和成就之一。這一點,衹要我們瞭解一下“醫聖”張仲景所做《傷寒雜病論》和明清的“溫病學説”在中國醫學史上的崇高地位就很容易理解。東漢末年,瘟疫流行,張仲景宗族二百餘人,在建安以來的十年中,“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他“感往昔之淪喪,傷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采衆方”,撰成《傷寒雜病論》。這一經典著作的成就主要有二:一是確定了三陰三陽的辯證體系,確立了中國醫學認識疾病傳變的基本原則;二是改變當時流行的針砭和汗吐下等簡單療法,針對當時的“傷寒”等疾病,以有論有方的形式,創立了二百餘首多有效驗的藥方,其中傷寒方一百一十三首。爲後世的臨床治療,特别是外感熱病的治療,奠定了基礎。宋以後,隨著張仲景及其《傷寒論》日漸被聖化,出現了盲目尊崇《傷寒論》的現象,妨礙了時人從多元化的角度去認識外感熱病的病邪。宋金時期,特别是十三世紀初,中國再次遭遇瘟疫多發時期,劉完素等醫家在長期的治療實踐中,感受到大量熱病的存在,遂依據《內經》的論述,提出了“火熱爲病”的觀點。而在明末的大疫中,吴有性在進一步依托《內經》,結合金元醫家的經驗,完成了《瘟疫論》一書,開創了明清時期的“溫病學説”,這一學説經清代溫病四大家爲代表諸多醫家的發展,取得了很大成就,對瘟疫等外感熱病的病原(病邪)、傳變方式和治療方藥均作了系統而理論化的論述,由此推動了整個中醫治療學的向前發展。參閱范行准:《中國醫學史略》,中醫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三—四十八、二百一十八—二百四十頁;廖育群:《醫道岐黄》,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百五十九—一百七十八頁。
除了醫療理論的發展,在人工免疫、醫藥資源與技藝等方面,也漸有進展,宋元以降特别是到明清時期,還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變化,這主要體現在:一是從十五世紀開始,發明并日漸普及了種人痘這樣頗具成效的防治天花的辦法;二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和醫學知識的相對普及,爲民間社會提供了相對豐富的醫療資源,醫療書籍大量出版,醫生數量大量增多;三是成藥製造技術的發展和相關製造與行銷店鋪的日漸增多,爲應急治疫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參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一百六十三—二百一十九頁;鄧鐵濤主編:《中國防疫史》,第一百五十一—二十一十三頁。。
上述中國歷史上的疫病應對經驗,可以説內容頗爲豐富,而且很大一部分,還沿用至今。故現有的研究往往對中國傳統的防疫經驗大加讚賞,比如張劍光在“中國抗疫簡史”中稱:“三千年來的歷史證明,中國是個勇於并善於抗擊疫病的國度,有著戰勝各種傳染病的傳統。” 張劍光:《中國抗疫簡史》,新華出版社,二〇二〇年,第四頁。
歷史地看,這樣説法當然是有道理的,中國在傳統時期,這方面的成績顯然不輸於其他任何民族,或許這正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社會何以没有發生諸如歐洲的黑死病(鼠疫)和美洲的天花那樣對社會造成結構性影響的瘟疫。但我們似乎也不宜過於拔高中國歷來的抗疫成就,爲此而沾沾自喜。首先,上述舉措、經驗是從歷史長河中衆多的史料中“精選”“集粹”出來的,并不是中國古代社會每遇瘟疫,都會普遍采用的。今天很多人在考察和評估中國古代的防疫舉措時,實際上是將不同時空中發生的經驗彙集到一個平面來進行的,由此得出的認識,難免會有失偏頗。其次,衹要進入歷史的情境,便很容易看到,面對瘟疫,當時社會展現給我們的更多的是恐慌失措和人口損失,而比較少行之有效的積極防控。對此,我們不妨以比較晚近的嘉道之際的大疫爲例,來做一説明。這此真性霍亂的流行在道光元年(一八二〇)達到高峰,當時時局尚屬穩定,而且恰逢新君旻寧登極未久,但面對大疫,官方的應對,在北京,衹是道光諭令京師的官員,俢和藥丸施送,買棺殮埋路斃尸體。而地方上,也不過零星地看到有些官員和民間社會力量延醫設局施治或修治丸藥分送 參閱拙稿:《嘉道之際江南大疫的前前後後——基於近世社會變遷的考察》,《清史研究》二〇〇一年第二期。。而且前面已經談到,因爲種種原因,國家并没有形成一套由公權力介入的可以强力推行的體制機制。
由此可見,儘管我們取得了很多成績,但也不得不説,中國社會并没能集腋成裘,總結發展出一套系統的疫病防治舉措,并催生出現代衛生防疫機制。特别是在最核心以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和保護易感人群爲要點的疫病傳播防控上,似乎乏善可陳,當時比較多采用的施醫送藥、散布醫方等舉措對於控制疫病傳播來説實際上未得要領。而且限於當時對於疫病傳染機理認識的不足,同時也出於道德人倫上的考慮,當時社會不可能鼓勵甚至還可能反對人們去關注推動疫病的隔離全面推行。
就此,我們不難總結出傳統抗疫以下三個特徵:一是國家一直重視對疫病的救治,并往往會根據實際情况作出應對,但出於技術和理念等多方面的原因,并未對防疫作出具體而系統的制度性規定,而比較鼓勵民間社會自行開展疫病的救治。二是中國社會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積累了豐富而值得肯定的疫病應對經驗,但這些經驗基本是零散、感性而片段的,缺乏系統的整理和總結,未能發展出體系性的疫病救治知識。三是針對疫病防治的關鍵環節檢疫隔離,雖然出於直觀的感知和本能反應以及某些特定的目的,出現了大量躲避、隔離乃至檢疫的行爲和事例,但這樣的做法,不僅一直没有得到主流社會和思想的鼓勵和支持,使之在理論和實踐上取得發展。
十八世紀以來,在科技進步和社會經濟文化整體性發展的基礎上,西方國家通過積極應對鼠疫、霍亂和流感等傳染病的侵襲以及勞動力健康狀况不良等問題,逐步發展出來了一套以預防和控制疾病爲基本內容的現代公共衛生機制。而中國社會,從十九世紀下半葉特别是二十世紀開始,伴隨著西方文明影響的不斷深入,源于西方的現代公共衛生觀念和機制日漸被視爲科學和文明的象徵,并在不時爆發的霍亂、鼠疫和天花等烈性、急性傳染病的直接促動下,得以引入和創建。其中清末東北鼠疫的爆發和防控,對於推動這一進程,起到里程碑性的作用。當時,東北有日本和俄國兩個殖民勢力在南北分庭抗禮,局勢頗爲複雜。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冬,鼠疫爆發後,殖民勢力以防疫爲名,强力擴張勢力,并對中國人進行諸多歧視性的管控。爲了避免主權遭受侵蝕、中國的國際形象受損以及保護華人的權利,清政府全力開展救治,由外務省右丞施肇基邀請馬來亞華人、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伍連德前往哈爾濱主持防疫工作。在東三省總督錫良的支持下,伍連德領導防疫隊伍采取了檢疫、隔離、阻斷交通、消毒、滅鼠、掩埋或焚燒尸體等近代衛生防疫舉措,在奉天建立的近代性質的奉天防疫總局,除開展防疫活動外,還發布了衆多有關鼠疫流行的統計資料。另外爲了防止東北鼠疫的擴散,在京城還設立了臨時防疫總局。不僅如此,在鼠疫基本熄滅後,清政府外務部、東三省防疫事務所於一九一一年四月三日至四月二十八日在奉天府(今瀋陽)隆重召開有中、美、英、俄、法、日等十一個國家參加的萬國鼠疫研究會 資料可見於奉天全省防疫總局編纂的《東三省疫事報告書》(奉天圖書館印刷所,宣統三年十一月)。以上參閱余新忠等:《瘟疫下的社會拯救:中國近世重大疫情與社會反應研究》,第二百六十一—二百七十八頁;焦潤明:《清末東北三省鼠疫灾難及防疫措施研究》,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改變了以往官方缺乏專門管理民衆健康事務的機構和職能的局面,逐漸在中央和地方設立了掌管醫療衛生事務的衛生行政部門和專業的防疫研究機構,師法日本等國,創建公共衛生法規,開展以清潔消毒、檢疫隔離、人工免疫、疾病統計、流行病調查乃至疫病防控體系建設等爲主要內容的衛生防疫舉措,以及以提升民衆衛生習慣和意識、改善環境衛生爲基本內容的群衆性衛生運動。原本屬於個人事務的衛生問題開始變成了關乎民族興亡的國家大事,藉由現代公共衛生機制的引建,國家成功地將原本民間的、零散的、非制度性的衛生防疫觀念和行爲納入到了官方的、制度化的體系之中,實現了民衆身體的日漸國家化,以及國家職能的具體化和權力不斷擴展。 以上參閱余新忠:《清代衛生防疫機制及其演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第九十四—一百二十六、三百二十二—三百二十八頁;余新忠:《真實與建構:二十世紀中國的疫病與公共衛生鳥瞰》,《安徽大學學報》二〇一五年第五期;(日)飯島涉;朴彥、余新忠、姜濱譯:《鼠疫與近代中國:衛生的制度化與社會變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第二百二十九—二百四十八頁。
四、中國瘟疫史的省思與啓示
從上述可以看到,儘管在漫長的歷史時期,面對瘟疫,中國社會没有坐以待斃,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做出種種積極的應對,而且也逐漸累積了比較豐富的舉措和經驗。不過若站在今日的立場上來説,卻很難對於傳統時期的疫病應對的成效給予較高的評價,若要説有“戰勝各種傳染病的傳統”,實言過其實。特别是從疫病實際控制的角度來説,大概很難説傳統的疫病應對具有多少决定性的成效。不難想見,要對瘟疫防治産生控制性的成效,至少需要以下三個條件中的一個:發明并生産出足夠多的有效疫苗,發現或研製出特效藥,調動社會有效資源實行嚴格而精准的現代衛生防疫機制。顯而易見,上述三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條件,傳統社會都不可能具備,而且就其采取的舉措來説,還差距甚遠。在這種情况,人們對於當時的疫病防控,又怎麽可能有太强的實際性防控成效呢?
當然,我們這樣説,并不是要站在現代的立場上去批評或貶斥古人及其努力,而是希望表明,對於歷史的評價應該實事求是,應該盡可能深入細緻地歷史事實做出理性而符合歷史實際的分析,若大而化之地説一些空洞的套話或盲目拔高,不僅可能會降低歷史的可信度,而且也會妨礙人們真正從歷史中得到有益的啓示。實際上,我們對梳理歷史的真正目標,其實也不是爲了找到解决現實問題具體而技術上的答案,顯而易見,科學技術、物質材料、生態環境乃至社會結構等都處在不斷發展變動之中,具體的歷史經驗其實很難有效救濟現實。不過在人類社會中,任何的灾异、物質和技術,都需要通過人和社會才可能産生影響和意義,瘟疫的危害,絶不衹是對個體健康和生命的傷害,而社會對瘟疫的應對和防治,也絶不是僅僅依靠醫療衛生技術可以完成的。顯然,瘟疫造成的影響和引發的社會和個體的種種反應,古往今來,往往具有相當的共通性,從歷史的觀察中去發現人性和社會複雜性及其對於文明價值和人倫道德的構建啓發,或許是我們梳理和考察這一歷史最大的價值。就此而言,通過對瘟疫史的省思,大概可以得到以下歷史的啓示。
第一,國家對救疫在制度上的缺失,既反映了傳統國家在統治理念上缺乏對民衆生命的真正關懷,同時也是承認自身能力不足的務實之舉。前已述及,在傳統時期,國家在制度上,缺乏針對疫病防治的具體規定。而且宋元時期在疾病救助上相對積極的政策,到了人口更多、瘟疫更爲頻繁的明清時期還變得日漸消極了。個中緣由,如前文如述,大致有二:一是瘟疫雖有礙民生,但畢竟不像水旱蝗等自然灾害會對王朝的統治産生直接的危害。二是在當時的社會醫療條件下,官方實際上難以全面擔負起複雜的疫病防治責任。一方面,官辦醫療機構效率和能力有限,不可能滿足民間疾疫救治的實際需求。另一方面,瘟疫的救療在技術上要比饑寒的賑濟複雜得多,不僅存在著疫情千變萬化和病人個體性差异等複雜性,而且古代醫療資源存在著很大的地區不平衡性,而當時的朝廷也難以具備進行跨區域調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中醫治療講究陰陽、寒熱、虛實、表裏,若不能對證施藥,可能會適得其反。在這種情况下,與其作統一的規定,反而不如聽任地方社會相機行事。
從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省思:其一,古代王朝雖然常常以“仁政”“愛民”相標榜,但其施政的真正出發點還是江山的穩固,一定意義上,所謂的“愛民”不過是“愛江山”的托詞。當然也可以説,衹有保持社會穩定,才能保障民衆安居樂業,維護江山穩固,不也是“愛民”嗎?這當然也不能説没有道理,但問題是,衹要對民衆生命的危害并不會對江山的穩固造成嚴重的危機,即使危害嚴重,也不會成爲施政的重點。對古代國家來説,疫病的防治固然存在諸多困難,但也必須説,國家似乎也没有意願傾全力來開展攻堅克難的工作,至少并没有像應對其他灾荒那樣用心。可見,在傳統的統治理念中,個體其實衹是追求整體社會安定的道具而已,生命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其二,歷代王朝未對瘟疫救治做出比較剛性的制度性規定,自然反映出了其在統治理念上的問題,不過就技術層面上來説,亦可謂是其在體認到瘟疫防治的極端複雜性的情况下,承認自身能力不足,放下無所不能的虛嬌後的務實之舉。明清朝廷在醫療政策上的相對消極,應該也是緣於社會力量在這方面救助日漸增强所産生的彌補效應。這在事實上,爲民間更具靈活性和實效性的救療開啓便利之門。
第二,因勢利導,較好地發揮了民間社會力量在瘟疫防治中的能動作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官民之間的良性互補。以上的論述已經表明,從官府的角度來説,中國古代的疫病防治應該説并無傲人的成績。不過因其能意識到自己的不足,而大力倡導和鼓勵民間社會力量來承擔瘟疫的防治任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多少彌補了其在這方面的失責。這種做法較好地激發了民間社會力量在防疫等公共事物中貢獻力量的積極性,利用了日漸興起的民間社會力量,特别是鄉賢,促使其扮演更爲積極的角色,借助比較豐富的地方醫療資源和日漸興盛的慈善力量和組織,開展了形式多樣的疫病救療活動,對於維護瘟疫中民衆的生命財産安全無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給民間社會力量發揮其活力和智慧留下了一定的空間,促成了疫病救療的近代演進。
民間社會力量因爲其能動性和靈活性以及更接地氣,往往能起到國家救療難以起到的作用。而且,民間社會力量活動往往是在官府的倡導下展開的,鄉賢在舉辦救治活動時,所預期的乃是讓自己更受官府的器重以對地方社會事務更具影響,而非希望自己成爲與官方對抗的民間領袖。發揮民間社會力量的作用,有序地包容甚至鼓勵民間社會力量,并不必然造成國民之間的對立。對此,我們可能需要從合作和互補這樣一種認知來看到明清國家和社會關係以及民間社會成長的意義。其意義,主要在於有針對性地補充官方行政能力的不足,并有效地表達地方社會的要求或民意,促發地方官員關注并舉辦一些缺乏制度規定但實際需要的事業。
第三,近代以降,國家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引建了現代衛生防疫制度,意義重大,但其實際也是國家權力的擴展與深化,若缺乏對其限度的充分重視,亦可能造成嚴重的危害。民間社會力量雖然在疫病救療中能夠發揮其積極的作用,但其弱點也是顯而易見的。首先社會力量在時間和空間上分布不平衡;其次,社會力量的活動多爲自發的,具有隨意性;再次,社會力量主要表現爲民間力量,其本身也不具有任何强制力。因此在疫病救療、某些預防衛生觀念和設施的推廣和醫療的管理等方面,其作用的發揮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極大的限制,從而嚴重地影響某些富有成效的觀念和舉措普遍及時的推廣,以及對衆多有害健康行爲的禁止和制約。因此,清末以來,在中國社會自身發展和西方文明影響雙重因素的推動下,國家對醫療衛生事業介入程度的不斷加深,逐漸建立了由國家主導,著眼于國家强盛的現代衛生防疫機制,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際效果上,都對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以及衛生防疫事業,起到值得稱道的推進作用。
這一進程,既是國家職能具體化,體現了國家的現代化,同時也是國家權力的擴張和深化。如果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其限度,也完全有可能這一現代化成效大打折扣,甚至走向其初衷的反面。首先,無論是國家還是社會力量,在開展衛生防疫時,都各有其優勢和不足,如果不能看到國家權力過度擴張的限度,而全面壓縮民間社會力量的空間,雖然有利於發揮集中資源、統一步調等方面的優勢,但卻顯然難以照顧到民衆具體而個性化的需要,不利於發揮民間社會的積極性和創造力去及時而有效應對防疫過程中層出不窮的問題,從而嚴重制約國家衛生防疫體制優勢的發揮。清末以來的歷史表明,繼承民間社會力量的疫病救療傳統,將其納入國家的制度框架之內,包容一定的民間社會的活動空間,對於整體的衛生防疫事業來説是積極有效的。其次,面對這種權利的擴張,若不能建立起相應的人民的監督和制約機制,那麽政府的職能往往就可能以現代化的名義“合理”合法地無限擴張,民衆的實際需求也就很難有制度和實際的保障,而容易使一些所謂進步和“現代化”成果,變得衹是看起來很美,而成爲對民衆來説的“水中月”“鏡中花”。最後,中國在近代公共衛生機制的引建中,關注點主要在於國家的强盛,這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且在當初內憂外患的情勢中,也有相當的合理性,但隨著國家的不斷發展,若不能及時地意識到衛生行政的目的本來是爲了讓國家更好地服務于民衆的健康,而不是相反,注意衛生防疫中個人的權利的保護,恐怕就會無助於更好地發揮公共衛生的積極意義,充分彰顯國家的人民性。
第四,暢達而有效的信息傳遞對防治疫情至關重要。考察瘟疫的歷史,特别近代以來瘟疫史,不難發現,瘟疫的危害不衹是造成了民衆健康的損害甚至生命的喪失,更重要的還往往由於疫病的傳染性以及其他社會文化和政治方面因素帶來的社會恐慌。所以每當發生大疫,社會必定會流言滿天飛。而要克服這一現象,除了國家和社會采取適切有效的應對舉措外,暢達而有效的疫情信息傳遞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實際上,及時有效而有針對性的信息發布,不僅有助於穩定民心,消除民衆的恐慌心理,同時也是國家和開展疫病救治舉措必要的基礎。這方面,受傳統的統治理念和技術條件等因素的影響,古代社會爲我們留下了深刻教訓。在古代中國,匿灾不報、粉飾太平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特别是對於瘟疫,由於缺乏制度規定,而且最高統治者也未必特别關注,隱匿不報的情况更爲嚴重,比如在清代江南,平均每年有244縣次發生瘟疫 參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六十八—七十頁。,但如此頻繁的疫情在《清實録》中卻鮮有反映。疫情無法“上達天聽”,必然妨礙國家采取可能的防疫舉措,也不利於更好地敦促地方官府和民間社會開展有效的救治活動。不僅如此,缺乏有效地及時的信息傳遞,還更容易導致嚴重的社會恐慌,比如在一八二〇年前後的全國性霍亂大流行中,由於國家和社會都無法對前所未有的疫情做出可信的解釋,“人人恐懼,訛言四起” (清)張畇:《瑣事閑録》卷上,咸豐三年活字本,第十一頁。“傳聞已甚一時,竟視爲豐都地獄”,甚至有人“因疫甚恐怖竟至自經” (清)鄭光祖:《一斑録·雜述二》,中國書店一九九〇年影印道光二十五年刊本,第二十三頁。。而且這種氣氛迅速擴散,彌漫著整個大江南北,從而給社會生命財産安全造成巨大的灾難。
第五,應歷史和人文地認識傳統時期多元的疫病和防疫觀念,不僅要看到其在歷史上的意義,同時還可以啓示我們疫病和防疫具有重要的社會文化性。前已論及,古人在防疫上,與現代相比,總體上比較消極,以“避疫”爲主。關於疫病的成因,大體有兩套認知系統,一是疫氣致疫,二是鬼神司疫。雖然中醫并不具備整體的疫病防控能力,不過歷史地看,其在救治個體病人、維護民衆正氣平衡等方面的意義,不容忽視,或許可以部分解釋中國社會何以没有發生諸如歐洲的黑死病和美洲的天花那樣對社會造成結構性影響的瘟疫。“鬼神司疫”作爲一種文化觀念,認爲瘟疫由鬼神來掌控,人間瘟疫的發生乃是因爲“乖違天和”“人事錯亂”或“道德失修”等。雖然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這樣的認識在今人看來,無疑可以歸入“封建迷信”之列,但如果將其置於歷史的語境中來加以理解,應該説,其對於當時社會的瘟疫應對是頗有意義的。一方面,這樣的觀念對於疫情中人心的穩定和社會的倫理道德建設多有助益;另一方面衆多流傳廣泛的鬼神故事,實際上包含不少合理的防疫內涵,比如前述疫鬼害怕大蒜,疫鬼一般無法破空而行,等等,都具有一定的實際防疫效果。指出這一點,當然不是説我們今天還應該相信這些所謂的“迷信”,而是認爲,它可以啓示我們,疫病本身并非純粹的生理現象,同時也是社會文化的建構,疫情也不衹是自然現象,而是與文化觀念、人倫道德等社會文化因素等密不可分的有機整體。故而,疫情的應對,僅僅依靠科學和醫療衛生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而必須結合社會人文力量綜合地開展。
第六,引入歷史視野和維度,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和思考人與瘟疫的關係,對現代性少一些驕傲,多一些對歷史和自然敬畏。前已述及,在中國傳統有關瘟疫的認識中,“鬼神司疫”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觀念,瘟疫往往被看作天神對於世間“有違天和”“人事不修”的懲戒 參閱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與社會:一項醫療社會史的研究》,第一百零六—一百一十、一百一十七頁。。無獨有偶,在《聖經·啓示録》中,瘟疫作爲天啓四騎士之一,也被視爲上帝對人類的警示 (英)弗雷德里克·F·卡特賴特、邁克爾·比迪斯著;陳仲丹、周曉政譯:《疾病改變歷史》,山東畫報出版社,二〇〇四年,第三、二百四十二頁。。雖然在顯微鏡發明和現代病菌學説出現之前,古人對於瘟疫的致病機理可以説還處於一種懵懂狀態,并不瞭解瘟疫乃是由自然界的致病病原體,即病原微生物導致的,從而意識到,瘟疫病原體與人類都是自然的組成部分,都是自然的一份子。但經由他們長期的對於天道和人間觀察和思考,以人類的智慧努力將一種自然與人間相互作用引發灾難性現象轉化爲有意義的文化力量。雖然我們很難確定地評估這樣的瘟疫認知對於一個國家乃至人類社會發展具體而確定的影響,但毫無疑問,對於統治者乃至人類的恣意妄爲來説,這肯定是一種非常有意義的制約性力量。
不過,隨著時代的推移和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人類對自身征服能力的信心也不斷高漲,特别是二十世紀以後,抗生素的發明和人工免疫的推廣,讓人類在應對甚至消滅某些傳染病方面,取得了突破的性進展,不僅對付衆多細菌性的疫病有了特效藥,還讓至少危害人類千餘年天花退出了歷史舞臺,脊髓灰質炎也幾近絶跡。這些巨大的勝利,一時讓人類對應對疫病的信心爆棚,以爲到二十世紀末,困擾人類數千年的瘟疫將不再成爲人類的重要危害。傳統作爲上天警示、啓示力量的瘟疫,也就成了人類意欲也可以征服的敵人。
然而,歷史的發展并没有人們想像的那樣樂觀,瘟疫這一“不速之客”,并没有因此而遠離人類。二十世紀以來,伴隨著人類對付瘟疫能力的巨大提升,瘟疫不僅没有减少,反而頻次在不斷增加,而且諸如西班牙流感、埃博拉病毒、SARS、MERS、禽流感、豬流感和新冠病毒等等新疫病,還一次次日漸頻繁而“行跡詭异”地造訪人類。這看起來似乎令人訝异,但稍作仔細考量,其實也十分自然。現代科技的發展雖然大大提升了我們對付疫病的能力,但同時,現代社會所帶來的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展,生活方式快速變動,以及流動性及其相應的不確定的加劇,也使得人與自然的關係更爲複雜,疫病流傳的機會更多,防控疫病的難度更大。晚近以來的歷史明顯提醒人們,瘟疫絶不是一個可以輕言征服的敵人,而若進一步拉長觀察歷史的維度,就更可以看到,人類長期積累起來的智慧,其實絶不是可以因爲一時科技的發展而輕易弃之而不顧的。既然我們已經非常清晰地瞭解到,瘟疫不是别的,而是病原微生物,它與我們人類一樣,是自然的一份子,而且長久以來,始終與人類共同構成同一個自然世界,那麽,衹要我們稍稍抑制一下完全自我爲中心的人類的自大和驕狂,就應該以現在不一樣的方式去重新思考人與瘟疫的關係。縱觀歷史,一部瘟疫史,就是一部人和瘟疫不斷追求相互平衡并達致平衡的歷史,同時又是一部由於氣候變化、人類活動範圍和生活方式改變等因素平衡不斷被打破,又繼續尋求并達致平衡的歷史。瘟疫自然不是我們的朋友,但似乎也不應被視爲要努力加以征服的敵人,它衹是我們必須學會與其共生共存、和諧相處的客觀存在。
今年年初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疫——新冠肺炎洶湧而至,肆虐於中國大地,席捲至世界各國,頓令神州失色,全球慌亂。遭此大劫,自是人類的不幸。但對於一個研究疫病與衛生的歷史學者來説,能夠有機會親身去體會感受疫情的衝擊與社會影響,也算是不幸之“幸”。筆者雖然研究疫病衛生史有年,不過近年來學術興趣已日漸轉移到醫學知識史的探討上,但突如其來的大疫,則不能不讓自己重拾舊日的議題,去思索和體會歷史與現實的關係。而當下處境和經歷,也確實推動我在既有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去進一步認識中國瘟疫及其社會應對歷史的特點和得失,去思考面對疫情,歷史學乃至人文學科的價值與意義。故而有了上述一孔之見。
歷史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遠航,我深深地知道,這些認識,主要是建立在自己對明清特别是清代瘟疫與衛生歷史相對系統研究的基礎之上的。從清代江南的瘟疫到清代衛生,大概在十四五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圍繞著這些議題在搜集、梳理和解讀相關的史料和文獻。對於清代的相關史料,自然無法做到全面掌握,但也相信自己有基本的把握。後來我將研究的視點向後延伸,力圖對於二十世紀的衛生做一鳥瞰式的概述,才突然真切地意識到,民國以降的醫療衛生史料,實不可與清代等量齊觀。這一方面自然可以説爲研究民國以降的醫療衛生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但另一方面,諸多的史料散見於各地圖書館和檔案館,而由於這方面的研究剛剛興起,相應資料的整理和彙編基本闕如,使得資料搜集相當地棘手。這些無疑會嚴重地妨礙這一研究的深入開展。有基於此,筆者深感,對於當下的醫療社會史研究來説,資料建設已日漸成爲當務之急,故一直期盼自己和學界同仁能夠有所動作,爲醫療史研究持續深化提供助力。兩年多前,有幸得到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及王錦錦編輯的幫助,開始協力編纂《中國近代醫療衛生資料彙編》,至今已出版兩編,凡六十册。今年又因疫情之契機,彙集了民國時期大量有關衛生防疫的圖書和期刊,分編五十册,集結出版,名之爲《近代衛生防疫史料彙編》。衷心感謝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在學術資料出版方面的遠見卓識,和對國內年輕的醫療社會文化史研究的鼎力支援。責編王錦錦女士在合作編纂過程中所表現出的職業、專業和敬業,則令人不勝感佩。
本資料彙編爲國家社科基金社科學術社團資助項目“瘟疫與人:中國經驗歷史啓示”(20STA030)的階段性研究成果,謹此説明。
是爲序。
余新忠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二十日於津門寓所